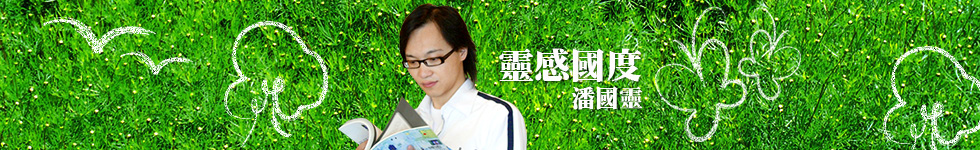城市精神
2013/01/14 10:13:00
網誌分類:
生活
| 人可以言及氣質,城市亦然,起碼在世界芸芸城市中,其中一些總予人較鮮明的形象性格,令人心生嚮往或者排斥。曾於香港大學任教政治理論的學者貝消寧(DanielA.Bell;非那個同命同姓、於二○一一年辭世的美國社會學家DanielBell,因易生混淆,故此一註),與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艾維納.德夏里特(Avnerde-Shalt)合寫了《城市的精神》(TheSpiritofCities)一書,結合社會文獻、親身生活經驗、街道行逛、質性訪談等多種方法,給九個城市書寫它們的城市氣質(ethos)。香港有幸是其一。 何謂城市氣質?似可感知卻難以言說的,但它不全然是抽象的。誠如該書兩位作者所言,城市氣質撒落於城市的建築、紀念碑、街道、鄰里之中,它們本身就有一種語言在傾訴着所在之城,向有心聆聽者傳達。如果這說法略嫌「浪漫主觀」的話,則城市的形象、故事亦處處可見於小說、詩歌、電影、旅遊冊子、歷史敍事之中;實質的社會數據亦提供不同線索,如一個城市在社會不同方面所投放的開支分配,一定程度反映該城所重視維繫、建構或傾斜的價值。城市氣質兼具審美和道德兩面,當然,城市不是單一的,兩位作者所寫的,主要是一個城市佔主導性的氣質(dominantethos),並不排除城市之中,不同種族、語言、宗教、貧富之間出現的斷層和差異。 「愛國主義」我們有一個詞叫「Patriotism」,「愛城主義」似乎仍無以命之,兩位作者以「Civicism」來稱之,中譯本把它譯作「市民精神」,以指稱對一份城市自豪感(urbanpride)。「愛國主義」去到極端帶來禍害,幾多罪惡奉它的命而來,但相對,「愛城主義」則比較無害,貝消寧說:「從道德角度來看,這種競爭與國家競爭相比,問題更少些,因為城市沒有自己的軍隊(新加坡是個例外),即使競爭的感情失控也不會發生戰爭。而且這種競爭常常是幽默的話題,能激發具有持久價值的文化創造。」事實上,不少城市就是與其他假想城市的長期或明或暗的競爭關係中,逐漸發展出自己的性格和特色。在書中,城市間不同的氣質,甚至可成為抗衡國族化、全球同質化的力量。以「我城」抗衡「國族」,這種力量香港應不感陌生,書中九個城市中,唯一同屬同一國度的,就是香港和北京。 九個城市,九種城市氣質,依據台灣財信出版社的中譯本,分別為:耶路撒冷:宗教之城;蒙特利爾:語言之城;新加坡:建國之城;香港:享樂之城;北京:政治之城;牛津:學術之城;柏林:寬容之城;巴黎:浪漫之城;紐約:抱負之城。各章娓娓道來,城市論述與個人生活札記相互交集,讀來頗有味道。篇幅有限,在此且補一筆,談中譯之不足。 原文蒙特利爾的氣質形容是:「TheCityofLanguage(s)」,中文如譯作「眾語之城」更為恰當,儘管也不強求。另一柏林原文形容為:「TheCityof(In)Tolerance」,包含其包容與不包容兩面,現在中譯取了其正面意義。牛津譯作「學術之城」也未必可取,書中有此言:「艾維納認為,牛津的觀點是學習而不是研究,是學問而不是出版」,原文把牛津比作「TheCityofLearning」,譯作「學習之城」比「學術之城」更恰當。最大問題則出在香港,原文的形容是「TheCityofMaterialism」,應譯作「物質主義之城」,中文譯本卻把它譯作「享樂之城」,實違作者原意,作者在前言中便有此說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仍然是讓香港不同於中國其他城市的驕傲之處,但香港式的資本主義並不是建立在自我利益或是享樂主義追求之上。」在香港那一章,作者亦特闢一節談及「沒有享樂主義的物質主義」,也就是說,在香港生活,物質很重要,但香港人普遍並無條件或心態享樂。譯作對原意的扭曲,或出於刻意求四字之公整,則無必要。可以的話,看書仍是看原文的好。 文、圖︰潘國靈 潘國靈 |
 | |
| |
 | |
|
回應
(0)
我要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