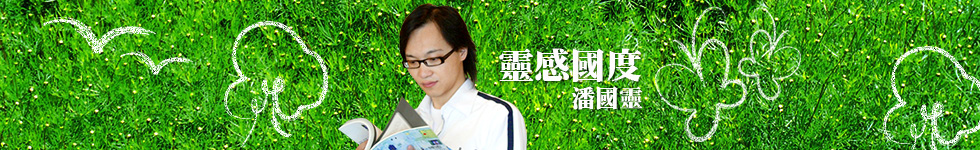疏離感與介入
2013/08/12 08:41:28
網誌分類:
生活
| 今天社會喜說「介入」,由街頭示威、社區保育、文學動員至面書筆伐等,都講求親身參與、投入,不僅止於冷眼旁觀。近看呂大樂教授的《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書中卻特闢一章「殖民冷經驗」,談論在殖民統治下,普遍市民生活經驗裏的一種疏離感。今天讀來,與當下「介入」、「行動」與「正義」論述三合一的社會氛圍頗相映成趣,也起着一點隔代衝擊的作用。 呂大樂說,社會論述多強調香港從寄居心態轉變為歸屬感的過程,而少有正視疏離感乃本土文化一個組成部份。作者在書中為疏離感「平反」,揭開其底蘊。作者重申,疏離感是殖民時代普遍市民的一種生活經驗,不能簡單被否定為冷漠、無態度、無意見,而有着更複雜微妙的歷史心理因素和演變。市民與殖民政府的疏離感不是單方面的,一方面是市民對早期殖民地政府不存好感,另方面也是殖民政府建立其統治霸權時,並無徹底要令被殖民者完全歸順之意。殖民者與市民生活互有區隔,在政治及文化上存有裂縫,市民不完全擁抱英國人的統治與文化,又與現實中國有區隔,其疏離感或模稜兩可感,甚至為香港日後的「本土」文化創造了條件。回到歷史脈絡,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前,依呂大樂說,市民與殖民政府及制度保持距離,其中不可忽視的是,親中共及親國民黨兩大陣營的存在,它們直接及間接地為民眾跟殖民體制保持距離提供了社會空間和物質基礎,亦為香港社會帶來了一個活躍的文化空間。待六七暴動後,加上經濟起飛,殖民政府改變治港方針,開始走進民間,社會才出現民情轉向,殖民建制才漸次成為國共兩大「市場」外的第三個選擇。 這一章的論述,為「疏離感」的消極抵抗性、文化空間的拓展性提供解說。在「介入」聲音高漲的今天,選擇重撿歷史為「疏離感」作詮釋,這切入本身其實也是一種疏離眼光,跟當下主流「反其道而行」,「保守」(並無貶義)也需要一點膽色。在檢視過去之餘,書中論述其實對當下社會亦可產生扣連,譬如說,書中提到當年拆卸告羅士打行,社會上並無引發出一種集體的懷舊情緒,中環的郵局總局亦如是,書中甚至有此一言:「維多利亞城在七十年代香港無聲無色的消失,市民也有其角色。」即是,不是建築物被保留下來才見市民角色,物事的消失不完全是官方的意志,其中亦有着市民的「默許」。以今天「文化保育」的眼光來看,這種態度也許是一種歷史「冷感」,但回到當時,這可能正是市民殖民生活的一種「正常」疏離感。反過來說,今天後來者對殖民建築的熱情,以至在脫離殖民地之身後,對英治時期竟逆向地產生無由的懷戀,也許又是那些從殖民過去生活過來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也許時代真的變了。呂大樂說:「那個殖民主義的環境的最大特點,就是它容許大多數港人與殖民制度保持一種距離」,把此話改一改,今天的處境也許是:「這個後殖民環境的最大特點,就是它強迫大多數港人與特區政府保持一種對抗。」距離感消除,埋身肉搏才是當下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而在社會兩極化、激烈化之時,疏離感或模棱兩可更無表述之聲,人們急於或被迫「站邊」、「表態」,遲疑者被遺棄,「介入」成正義之聲,政治正確修辭,同時又摻揉着各式喧鬧雜質的民粹噪音。與此同時,又常聞人說,現在的香港他們愈感陌生了,年輕人萌生出走之意(通常只是想像),如此「疏離感」,又與殖民時代不同。「介入」與「疏離」這兩極擺盪,可以續寫下去。 潘國靈 |
 | |
|
回應
(0)
我要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