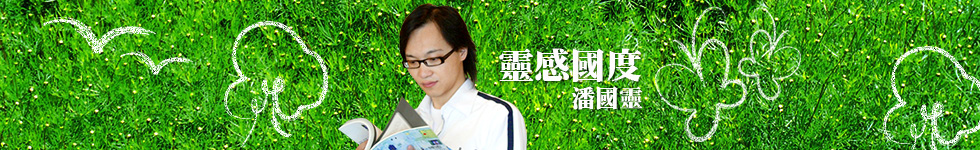不可割捨的實體書
2014/08/25 08:42:06
網誌分類:
生活
| 為「漂書節2014」擔任演講嘉賓,自擬了題目「不可割捨的實體書」,因最先想到的是,無實體書便無所謂「漂書」,雖然「漂書」這概念──將心愛的書流放出去讓有緣人遇上,跟愛書人多少有的「藏書欲」有點相違──心愛的書總是亟欲收藏的,有時甚至到了一個極端程度──連親密的朋友都不肯輕易借出。但這是別話,本文讓我淺談一下對實體書之戀。 早前在「香港書獎」頒獎禮中,某出版界人士頒獎時說到實體書向電子書的過渡,雖他說不會那麼快,但「過渡」二字聽來總讓我感到悲哀。我更寧願相信和希望的是,頂尖愛書作家阿爾維托.曼古埃爾(AlbertoManguel)在《深夜裡的圖書館》中所說的話:「不需要有紙頁的電子文本,可以跟不需要電力的書頁和平共處;在竭力為我們做最好服務之際,並不需要彼此排除對方。」關鍵是電子書和實體書如何分配,除了百科全書、字典、地圖集等天然地更適合以電子書存放展示之外,我更樂見更多速食讀物走到電子書中,讓實體書更具它該有的價值、形體和矜貴。 在為講座作準備時,我擬定了一些問題作開場白拋給讀者,諸如:(一)出門時你有沒有挑選一兩本書放進書包(或袋子)的習慣?(二)乘地鐵時有沒有看書(另類「低頭族」)?(三)以書作禮物,你多久沒有收到(或送出)?(四)旅行帶不帶書(旅遊指南除外)?(五)有沒有幾本書可訴說你成長故事的點滴?(如莎岡在《我最美好的回憶》中,在「閱讀」一章中談到了她成長期的四本書)(五)香港人喜歡放假去旅行,你曾否放假就只為了重讀幾本舊書?(六)書架上好久沒碰的書籍,你曾否心血來潮聽到其無聲呼喚?(七)有沒有「讀殘」一本書的經驗?(不是不小心所致,而是真的把書「讀殘」了,如古時孔子「讀《易》、韋編三絕」?) 問題可以一直問下去,但篇幅所限,就此打住。但可以預見,以上問題,都是與實體書連上的。我們素以身體來想像一本書,書有「書皮」、「書背」、「書脊」、「書衣」;所有愛書人都有「摸摸書」的心癮,捲曲的書角是你留下的標記,書籍發黃是時光贈給書和你的洗禮;一本書給你畫過、間過、在空白處寫下一點評注,就成了世上的獨一。生活在香港,愛書人大抵都經歷過為書本闢出空間的苦惱,但這苦惱中自有其挑戰,從中亦可理出一點心得。因為一本本書的實存,因此才有藏書票、書籤、書梯、書櫃、書牆、書店以至圖書館等,各項皆有它豐富綿長的故事,共同構建書的深厚文化和一整個宇宙。 以上所說並不是一個文化討論,即我並沒打算「客觀」探討諸如書籍的未來、網上閱讀(onlinereading)的意義等問題,並無應然與否或論述普遍化之意圖。在書本閱讀上,我自知自己頗屬「恐龍」一族,至今仍沒擁有過一個電子閱讀器、出門袋子裏一定帶書,旅行亦然;乘地鐵時我會為一車廂盡是熒幕發光而暗自悲傷。但這只屬個人的選擇或感觸。但這個人因素亦非與時代無關。骨子裏我懷疑自己根本就想做一個與時代有隔的人,英文所說的“anachronism”。時代日新月異讓我慢一點就可以了;資源增值「速讀」「泛讀」「實用閱讀」讓我仍保有「無為而讀」的空間就好了,究竟文學的其一本相於現世不就是「無用之用」嗎?3G後是4G其實你給我2G就足夠了。天天「社交」剝花生BBQ也挺辛苦的。古人說「惜墨」今天我提醒自己「惜照」尤其是時興的selfie。我也會上網搜尋讀點文章,但真正專注的美好閱讀時光我還是預留給紙本書。如果紙本書在電子科技面前象徵「舊事物」世界,也許年紀漸長,這舊世界好像已有我餘生也未可窮盡的豐富了。然而我並非拒絕進步。 潘國靈 |
 | |
|
回應
(0)
我要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