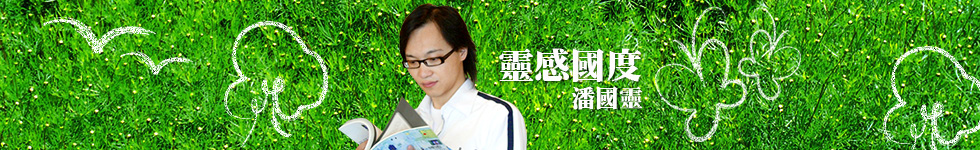鬼城
2014/07/28 10:11:28
網誌分類:
生活
| 「鬼城」(GhostTown),在西方解釋比較簡單,就是一個因社會或自然災難因素,遭破壞或廢棄之城,未必一定完全人去樓空,但整體蕭條景象如一座廢墟,氣數已盡,只能吸引異類遊客一睹頹敗之世相。 「鬼」在中國有更深厚、複雜的文化;我常想,如將「鬼城」代入中國語境,必可誕生更豐富的想像和創造。篇幅所限,或者遠的不別,就說我城吧,我城一向不缺充滿城市隱喻的「鬼魅寫作」(經典如李碧華的《胭脂扣》),近者,我們都知道,這一兩年有好些「鬼片」,都是充滿弦外之音的。 又是出於李碧華,《迷離夜》和《奇幻夜》真是「不看不看還須看」,其中最多人談論的是陳果執導的短片《驚蟄》,邵音音在鵝頸橋打小人打「梁震嬰」,在陰森中注入幽默,給許多香港人消了一口悶氣。晚明文人馮夢龍有云:「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雜」;落入我城異曲同工的有黃大仙靈簽:「何為邪鬼何為神,人鬼如何兩不分」;所謂「國之將亡,必有妖孽」,時近亂世,牛鬼蛇神掛着人臉,此亦是鬼氣可供發揮之一途。 當然,鬼不盡是惡鬼。人間鬼域,有時又通回文首所說的城市頹敗。麥浚龍導演的《殭屍》,過氣動作明星回到破敗的舊屋裏,屋內住着一個末代道士和殘餘老街坊,一切都充滿着頹敗氣息,屋裏的破落格局多少令我想起陳可辛《三更之回家》中的空置警察宿舍;同樣有樣故人「回家」的母題,可那個「家」即使回得去了,其實已是面目全非,守着一個家如守着一座廢墟,也許才是「家是香港」的一份執念。 氣數已盡,雖生猶死;人活着可以吊命,城市也可以。一切表面如常,但如果你生得一對「陰陽眼」,華麗但悲哀的城,到了晚間就變身一個「紙紮城」——這是彭浩翔《香港仔》中賦予我城的一個奇幻想像。當然,《香港仔》是「合拍片」,我們知道,國內不淮拍「導人迷信」的鬼片,電影也給坐上紙紮的士目睹紙紮城的楊千嬅一個心理學解釋,幻覺乃由精神疾患所致;但無論如何,單就「紙紮城」這意象,彭導這「擦邊球」也擦得蠻有意思。 如此說來,「鬼魂」這東西,竟也是香港創作自由、與內地文化身份區分之寄託。可以名正言順拍一齣「鬼片」,不理還原為甚麼科學、心理學解釋,原來也是可貴的自由。像張家輝首執導筒的《盂蘭神功》。中國人的「鬼節」真的從來都比西方的「猛」很多,份外嚇人也更堪玩味。這又牽涉「鬼」在中國文化裡的另一古老詮釋:「鬼之言歸也」。「鬼」與「歸」近音,其義有相通;只是人死離開塵世本是歸於大化,但在許多民間傳說、小說中,那「歸」又逆轉過來,變成因各種執念未能放開塵世的鬼魂返回人間。在《盂蘭神功》中,陰魂不散返回當下的就是一群四十年前在神功戲中活活燒死的火鬼。以為事過境遷嗎?厲鬼卻念念不忘,冤有頭債人主,於個人家族如是,如社會歷史亦然。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學說,這也可說是一種「被壓抑的回歸」(returnoftherepressed)。電影中的空間場景多是抽空的(據說拍於馬來西亞),但那明明又是香港的故事,也許這亦是另一種「鬼域」的意象——以為回到了家嗎?殊不知在「家」與「非家」之間,依弗洛伊德之說,此為之「詭秘」(uncanny),熟悉而又令人驚嚇,多少又應此情此景。 潘國靈 |
 | |
回應
(0)
我要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