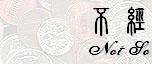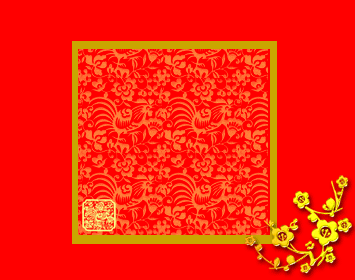四之二: 十八羅漢
終於輪到我接受檢查了。我踏進了陰暗的大門內,所有的東西全部翻轉搜查,筆、藥、鎖匙、 錢,甚至內外褲帶都被抽了出來,並且鄭重其事地一一登記。
一個荷槍實彈的紅衛兵將我和一個學生帶走——橫過鴉然無聲的正廳,進入東側的小門,便見一列四間的廂房,同樣地鴉然無聲,但可以見到每間都擠滿了人,他們坐在地上,一齊向窗外仰望著。在最後一間,紅衛兵開了門鎖,將我們推了進去。
燈光昏暗,我們好像進入了一個黑沉沉的洞穴。稍定神後,才看到這裏面其實也都擠滿了人。他們正在儘量地騰出地方來安插我們。我們只鋪得下一張單人的草蓆。環顧四周,發覺這其實並非外間所傳「老監頭欺負新監犯。」
房間的長度在四米之內,寬度不會超過二米半。腳對腳分成兩邊,一邊睡十人,另一邊睡八人。這八人的一邊,放著一個直徑約一米的大尿缸。
大家默默無言地盤膝而坐,中學生在我的身邊嘲諷著:「真像十八羅漢呀!」我苦笑著。
濕氣、臭氣、汗酸氣匯成一股令人作嘔的氣味。我就這樣地被丟棄在生活的另一個角落裏。
徹夜不眠,剛要入睡的時候,卻被一陣哨子聲驚醒。大家迅速地把被迭好放在背後,依然盤膝而坐,好像在等待著什麼。
不久,在我的對面有人拿起了老三篇,其他的人也跟著拿出來。可以看出,這裏也有領導,這人正是組長。他開始帶讀愚公移山。這時候,在別的房間裏也傳來了咿咿嗡嗡的讀老三篇的聲浪,以後,我們每天都是這樣開始的。
讀完了毛著,是各房——其實應叫監倉——輪侯大便的時間。
「兄弟夥!來到這裏就是一家人啦,安心改造,等待政府寬大處理!」他顯然在勸慰著我們兩個新來的人。「先說作息時間:五點起身,七點阿屎,每日兩餐,早餐九點,晚餐四點,其餘時間讀毛著,寫交代材料,夜晚九點熄燈睡覺 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在說著最後這一句最嚴肅的話時,他卻搖晃著巨大的腦袋,扮了個鬼臉,那本來細小的眼睛瞇縫成一道細線。
這組長,本來有一個很好的前途——做著地區專員公署的公安員。在中國,公安乃是使人肅然起敬,人人不敢側目而視的單位!而這公安員乃是權力的象徵。他可以掛著一支短槍。抓偷渡,抓走私,抓違法亂紀,以及一切他認為應該抓的人。
1958年大躍進之後,國家出現了暫時困難——因為只顧大煉鋼鐵而忘記了土地不會自己長糧食,所以,大家挨餓。就連這狠抓階級鬥爭這條綱的公安員家裏,也是父母水腫,弟妹肝炎。反觀那些早已被鬥垮鬥臭了的四類分子,卻多有海外親朋周濟些麵粉、豬油,個個顯得氣定神閑。他一氣之年,棄械偷渡。
不幸,他被戰友們抓了回來,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分析:此人出身貧農,苗紅根子正,斷無叛國投敵之理!想必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侵襲或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所擊中!但遍查之下又未發現這該死的糖衣炮彈來自何方。只得草草給個「開除黨籍,留隊察看,以觀後效」的處分,希望不久之後他能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站到無產階級這邊來。誰知一去杳杳,他再也沒有站過來!
從此,他一不做二不休,又連續偷渡了好幾次,雖被抓回來,由於上上下下各種關係,也就讓他有一條生路——反正,只要不判刑,農民還是有得做的!
這最後一次偷渡,初時似很順利,但船到香港附近,卻出了毛病,直至黃昏,還在海中漂浮,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忽聽見遠處有突、突、突的馬達聲,朦朧間見有一汽船駛近,一個個正慶倖著「天無絕人之路」,於是急忙呼救,殊不知船到跟前,卻見船身橫刷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標語!這樣他們的船便與祖國的船連在一起,被帶離了資本主義的深淵,回到社會主義祖國來進行挽救和改造。
時值清理階級隊伍之際,革命隊伍尚且清理,何況叛國投敵者!於是,被扣上手銬,押送來「譚公爺」。
據說,他進門的第一句話是:「十年水流東,十年水流西;有時抓別人,有時被人抓!兄弟夥,大家來食糖,每人二粒,勿相爭!」
糾察隊員們也只得任由他放肆一下,論輩份,他應是他們的師兄,師父呢!
在生產隊長旁邊,是自稱香港得雲茶樓的二等廚師,他剃著光頭,有一張佈滿皺紋的猴子臉。幾年前偷渡,在香港的一家酒樓當雜工。後來勾搭上一個寡婦,這寡婦的先生原是個刻苦耐勞的泥水匠,在一次作業中不慎摔死了,婦人得了兩萬元的賠償。二等廚師便把她、她的兩個女兒,以及所有的財產都接收過來,生活過得滿不錯。
這一年,忽然良心發現,記起了家中的老母及元配嬌妻,終於打了領帶,灑上香水,威風凜凜地回到故鄉,對於左鄰右舍、幹部領導都不屑一顧。時值清理階級隊伍,開了一個偷渡人員學習班,請他到學習班交代在香港所幹何事?錢那麼多,是不是參加了特務組織,領了活動經費?不交代清楚,休想回港!
自此之後,他也學乖了,總想找機會立點功,將功贖罪,好讓人們批准他返港。
他原是一個相當有名氣的舵公,他一住下來,便經常有人來邀他偷渡,他都一一檢舉揭發了——他以為,立多一些功,便可讓他如願回港。不過,事實並非如此,他等得沒了耐性,決心自己偷渡,那結果,是被關到這裏來。
儘管每月可由家屬送來一點日用品和半斤普通食物,但在我看到的半年多時間裏,從未見到監外有誰給他送來任何東西。他似乎不被當作兒子,不被當作丈夫,不被當作父親!
在寒風透骨的寒夜裏,看到他既無棉被也無 的衣物,只用麻袋複蓋著捲曲著,不停顫抖的身體,真為他難過!
幸而他有點小聰明,每天背誦「老三篇」的任務,也大體可以完成——雖然他唯讀兩年書,不過,有個地方卻幾乎永遠讀錯,那就是:常常不自覺地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讀成人民幣和半人民幣——自然,因此常常換來一頓痛打!
最喜歡和二等廚師過不去的是躲在暗角落裏的香港客。他常常強烈反駁二等廚師的信口開河,說他講大話!雖然不到三十歲,但時時以老香港自居。
年紀是比二等廚師小,但資格卻真的比他老。他從陸路越境過香港時,不到十五歲。做了十幾年紡織工,惹了一身病;在貧病交迫中倍覺孤獨與淒涼。
故鄉雖無父母,但每月都給哥嫂寄錢,想哥嫂也有些積蓄,回到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與哥嫂相依為命,應無問題。托人寫信給哥嫂,沒有回音,便匆忙動身回來。
如果他規規矩矩地回家去,甚至以自身的經歷大揭香港這個腐朽沒落的人間地獄,他不難成為批判帝、修、反的英雄,到處現役說法。
誰知半路停車時,他見周圍景物好似十分熟悉,突發奇想,覺得不如步行回家,可以給哥嫂一個意外的驚喜。所以,悠閒地沿著海邊走去。不久便碰到幾個放哨的民兵。人家見他西裝革履,態度悠閒,不似偷渡客,好意地勸他回頭。但他堅信自己沒有走錯路,還是雄赳赳地「勇往直前」。
事情就自然向常理發展。十幾分鐘後,他的後面風馳電掣般來了幾架自行車,這一下可不是耐心勸阻了,他被幾個威風凜凜的民兵叔叔強行帶走了。
起先,當他對於生活還懷著希望的時候,常常要講一講第一次被審問的情況,作為笑談。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一個同志拿著紅寶書(語錄)問他。
「這麼?這是 紅薄仔!」他覺得這與香港匯豐銀行的活期存摺何等相似!那東西,香港人俗稱「紅簿仔」!值得慶倖的是:革命同志對此並無所知,以至他竟然避過了十年徒刑!
「胡說!這是毛主席語錄!大家都要按照他老人家的指示精神辦事!」同志怒喝道,「現在告訴你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看你走哪條路!」
聽了這最後一句,他由衷地高興起來了!
「哎呀!你為什麼不早說?現在還可以自己選路走的麼?好,你開門哪,我走回家那條路,不走海邊那條路了!」說完,立即起身邁步。
「他*的!你是故意裝蒜,還是這樣沒有政治頭腦!」審問的人又好氣又好笑,舉手想打他,他嚇得一面躲閃一面叫道:「啊呀!不好打呀!你不是說要按紅簿仔 唔,對唔住,要按毛主席語錄辦事的麼?」
審問的人真的住手,真靈!
「好,不打了。你說說:為什麼有汽車你不坐,偏要行路?」
他摸了摸腦殼,覺得這一次決不能因為沒有政治頭腦而挨打了,得說些政治話才好。
「坐汽車麼?唔,坐汽車是國民黨;行路……行路是共產黨!」
好!這一下可暴露了反動的政治頭腦!他終於被連推帶打趕進了監倉。
開始的一兩個星期他還是有說有笑的。他盼望他的哥嫂也會像別人的親屬一樣,給他送點食物,帶件寒衣,甚至帶個慰問的口訊也好,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了,這一切終於都成了泡影!他不得不放棄所有的希望。在北風呼哨的寒夜中,顫抖著蜷縮在一方薄被單裏 直到有一天,我冒著挨搶托的危險,鬥膽向如臨大敵的管教員奉告時,他才得到了政府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加了一個麻皮袋禦寒。
他逐漸沈默著,最後,一句話也不說了。二十幾歲的青年,佝僂著背,臉色由白轉青,不停地咳嗽!
每月一次由家裏送到的半斤餅乾,雖則是我應該珍愛的東西,但我總是毫不猶豫地分一些給他。起初,他帶著歉意的微笑接受了。後來,有這麼一天,他臉色陰沈地將我丟過去的東西丟了回來。
「怎麼了?」我感到十分詫異。又固執地將東西丟過去(規定不准移位)。
「老這樣吃下去,我拿什麼還你?你也得餓肚子哩!」他把頭轉向別處。
「你想到那裏去了?我說過要你還的麼?」
我怕見鮮花的凋謝,我怕見樹木的枯萎,我怕見生機的衰竭……
飢餓真是一種可怕的東西,餓火終於把他的自尊心壓下去。他迅速地用被單蒙住了頭,在被單裏咀嚼起來,我不禁一陣心酸……
作為悲劇的主角是不幸的,作為悲劇的觀眾有雙重的不幸!
廿五歲的生產隊長是粗獷的農民型。尖嘴,新剃的光頭上有點點發亮的瘡疤。他犯的是因奸致命案。
他,團支部書記,保管員等幾個專案組成員,藉口政治審查,把地主的女兒叫到外面,強姦了。並且警告她「不准亂說亂動」「隨傳隨到」。
他們的警告,對於那少女來說並不陌生。她的有限的生活經驗以及歷次「運動」的教訓都令她明白自己生活的準則是:「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但是,肉體和精神是無法忍受這樣的折磨的。唯一可以傾訴的是自己的母親。但是,一個地主婆對此又將有何作為呢?她們只能像其他許多軟弱的人一樣,用消滅一切感覺的方法來消滅自己的痛苦!
某夜,地主婆在外地工作的兒子手持菜刀闖進生產隊想殺人(人們說:這叫階級報復),不遂,轉而偷渡去了……
他是罪有應得的,至於他是否會憤憤不平於對階級敵人毫不心慈手軟而遭懲戒,還是為自己的喪盡天良而悔恨終生,我們是不得而知的。
與生產隊長一樣忘本變質的是青草醫生。
此人被關進來時,穿著白襯衫和藍條紋的的確涼褲,打扮得像個香港客。有點歇斯底里。時而神氣活現,尖聲嘶叫,時而發著悲涼的調子。
沒想到他三十出頭已是某大水庫工地的黨委書記。據說,因為與縣委某領導互相爭奪工地的女出納員成仇。
後來,某領導買通了女出納員,在某次會議上,採取突然襲擊的方法,製造大量假材料,誣告他貪汙公款,並且由出納員親自證實與青草醫生通姦。這樣,他被推光了頭,抓進看守所。
幸而,貪污公款後來被證明是誣衊不實之詞。通姦則難落實。宣佈無罪釋放後,調公社做團委書記。這一次卻飛來豔福。有一個父母在香港的少女竟然迷戀上這位有婦之夫。兩人終於決定偷渡。不過,並沒有成功,他們在半路上便給抓了回來。
寬大處理,給了個留黨察看的處分。他卻大鬧黨委。
留就留,滾就滾,察看什麼?一怒之下,回家種田去。
好在他有家傳的中草藥驗方,特別是醫小兒麻痺症的驗方。幾乎手到病除。
幾年間,他在沿海小鎮,被視為神醫,賺了不少錢。
他賺錢的方法也很高明。醫好了小孩,父母問到要多少酬勞時,他總是說小意思,隨送吧!
幾劑草藥,成本不超過一毛錢,假如你問人家要十元八元已屬牟取暴利;倘若你自願地隨便送點,那麼,一條人命,一個寶貝兒子,該值多少錢呢?人們只得盡其所有地送禮,並且一輩子覺得欠他的人情。
有一天,一個多時不見的遠親帶來了一個年老體弱的人,請世侄幫這老人偷渡香港與兒女團聚,這在他已易如反掌,因為感恩圖報的漁民很多,他只需招呼一聲,不愁沒人辦理。落船之前,這老人感激涕零,邀他同去享受榮華富貴,但他謝絕了,他覺得自己正享受著榮華富貴呢!
他沒有想到,他放走的是一個正在被批鬥的地主分子!
不能說我都鄙視這些人,但,我的同情顯然在另一些人身上。
縣籃球隊隊長、電影放映員、高高瘦瘦、溫文爾雅、常帶羞怯之情,他的案情與我類似,比我簡單,但卻更催人淚下。
這放映員,有一個老同學,出身剝削階級,被送勞改。釋放後,變成「勞改釋放犯」,生活無著,放映員雖膽小怕事,不敢與他正面接觸,卻經常暗中接濟他。這人後來偷渡香港。大約出於報恩,這人經常寄些東西給他——自然是由他的嫂嫂或其他親戚轉給他。
今年六月,這人因為太久未收到大陸的妻子的信,托人轉來一信,問及妻子「是否因為天氣太熱,感冒了?」
這「膽小心細」的放映員猜想:「天氣炎熱」何以就一定「感冒」?即使感冒,何至於不會寫信?想必當時「清理階級職隊伍」的氣候傳到香港,這「勞改釋放犯」及「叛國投敵」分子深恐自己的家屬牽連其中,來信探問。
放映員覺得不覆信不好,說清楚又恐「洩露國家機密」,戰戰兢兢仿照來信的隱喻寫了一封短信由妻子抄妥寄出。其中提到:「近來確因天氣炎熱,我也感冒了,又兼有些腦病,請勿再來信。」
此信被公安局截住,他馬上被抓起來並作為觀行特務活動立案。在我未被抓進來之前已知道此事作為「縣無產階級造反派的戰果」廣泛宣傳,說是「無產階級的天羅地網使一切暗藏的階級敵人無所逃遁」!
一同被捕的還有:他的妻子——抄寫反革命信件;他的嫂子——接轉反革命活動經費;以及,來到世間僅有三個月的女兒——因為未曾斷奶。
這樣,他的家裏便留下八十多歲的祖母,五歲的女兒,三歲的兒子。假如說這叫「妻離子散」,恐怕有「同情階級敵人」及「污蔑社會主義制度」之嫌,那麼,讓我們在良心的字典上找尋更恰當的詞句吧!
他不停地寫「坦白交代材料」。因為他永遠寫不出「香港特務機關的名稱,聯絡人,暗號,」也解釋不了他信中的暗語包含了多少足以使「千萬顆人頭落地」的「國家機密」。雖然我往往以「專案人員」的觀點暗中對他的材料作了提示和修改,也無法很快地滿足他們的要求。
荒郊野嶺的冬夜,寒風透過堵塞不盡的小孔切割著人的肌膚。他擁著堅硬的棉被,把稿紙攤放在大腿上,蜷伏著身子,不停地寫、寫、寫。唯有不時傳來的他的缺乏乳汁的女兒的飢餓的哭聲才使他擱筆,側身細聽
最後被關進來的,應該是「英文老師」了。當時正流傳著「211」即將解散的消息,因為,據說「鬥、批、改」已發展到了「改」的階段,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大有希望放出去「改」。沒想到還在繼續抓人,而且竟然又抓得那樣離奇古怪!
他與同校的一位老英語教師交往甚密。某夜,兩個紅衛兵帶著老教師闖進他的家裏。
「他說放了一包秘密檔在你這裏,快拿出來!」 紅衛兵指著老教師。
這青年頭昏腦脹,怎麼也想不出曾經有過這麼一回事。但那老教師硬說有,並且指明就放在靠窗的壁櫥。紅衛兵翻箱倒櫃,結果,自然是什麼也沒有。
「拿出來吧,你轉移到哪裡去了,那東西對你並無用處,你何必替別人受罪呢?」這兩個紅衛兵真是難得一見的好人,竟然好言相勸,說服教育!
我們這位認為人生如蜜,人生的圖畫都是直線條的青年人,此刻真是又急又悲傷,他的聰明才智竟沒能讓他在此刻找到任何可以說明真相的詞句,只是淚流滿面地連聲說道:「沒有,沒有呀,你為什麼害我呀」
沒有?怎麼會沒有?他為什麼不指控別人,偏指控好朋友?「沒有」就是狡猾,而狡猾便是敵人 這是被廣泛運用著的推理。
於是,不由分說,將他鎖上手銬,帶到縣裏,與骨肉生離死別的痛苦自不待言,更糟的是:三天後便是他的婚期,新娘遠在潮州,此時正整裝待發,盼朗迎娶
無論如何,我已多了一個休息時可談一點文藝的夥伴。
我將懷著深深的感動與愛來回憶另一個人。
他睡在我的近旁。瓜子臉,大眼睛,薄嘴唇。經常穿著圓花圖案的淺黃色睡衣,活像一個剪了短髮的小姑娘。
十一、二歲,當「三年暫時困難」的時候,不明不白地被他的哥哥拉上了去香港的帆船。兩人同在香港的電鍍廠打工,雖然辛苦,收入卻不錯,除可養活自己,寄錢養家也綽綽有餘。
父母的年紀一天天增加,思念兒子的感情也難以抑制,千萬封家書迫他們回家團聚。這兩個孝子終於捨棄香港的一切,帶著布匹、單車、手錶、縫紉機等等,「滿載而歸」!
時逢「清理階級隊伍」,大家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一分析:在香港那樣一個人吃人的人間地獄,小小年紀未被迫害致死,已是十分幸運!如非幹反革命勾當,無理由這麼「發達」,還是抓起來審查為妥!
除了懷念父母和擔心他的哥哥,他實際上並無太大的煩惱。不過,有時聽到別人判了徒刑,他也會變得心事重重起來。
「哎,我會不會走那條路呢?」他會突如其來地問。
「這裏的人算你最乾淨的了,你會第一個回家。想那些事幹什麼?」
「要是我出去,人有問我犯什麼罪,我怎麼說呢?」
「你年紀還小,主要是你哥哥的責任。」
「無罪麼?無罪怎麼會坐監呢?不判刑也會被叫什麼分子的!」
有時晚上熄了燈,他會湊到我的耳邊咕嚕一陣。
「聽說去勞改更好呢!」
「你想到哪裡去了?」我大吃一驚。
「他們說,勞改可以活動,曬太陽,吃得飽,不像我們老是餓肚,動也不可以動一下,」我彷彿見他愁眉不展,臉上籠罩著陰雲。「不知有沒有人自己要求去勞改?」
諸如此類,儘是些不著邊際的、陰沈灰暗的幻想。當然,有時候,這些幻想也人以比較明快的色彩表現出來。
有一天,他獨自坐著出神,臉上浮現著天真的微笑,我問他正在想什麼?
「我在想,現在,我睡著了,人家總喚不醒,但是哨聲輕輕一響,我就隨即醒來。將來回家去,母親要喚醒我這死豬就艱苦了!我還是在縣城先買一個哨子,到家裏,同哥哥、弟弟輪班。早上,哨子吱吱一吹,大家都起身,免費氣!哎,乾脆,吃飯也吹哨子吧,吱——吱,吃飯了!大家便拿著碗筷圍攏來」
這樣一個稚嫩純潔的靈魂,想不到竟然在這樣的地方以這樣的方式來認識人生!
他算是比較幸運的了。國為他是我們當中被最先釋放的一個。當這個他日盼夜盼的,理所當然的消息傳來時,他卻感到十分意外,甚至不知所措,慌亂起來了。為了使他免受責罵,我趕忙幫他收拾行李,他則一面心神不寧地把東西抓起又放下,一面偷偷地對我說:「你真好,你最好!人人這麼說,將來你出去,要來看我啊!」
他偷偷地,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他家的住址,他父母的姓名,他家的周圍環境,以便我很快找到。他要我一遍一遍地背熟(因為倘一動筆,便有「通風報信」之嫌,罪加一等,大家都走不成!)
「記住啦,我一定去看你的,也探望你的父母!」
在「管教員」兇狠的催迫下,他終於背起了沉重的鋪蓋,手提著裝在臉盆裏的雜物,蹣跚地邁向門外。「監倉」的門打開,他原本低垂的頭驀地回轉過來,深沉地望住我,那眼睛分明在問:「記住啦?」
我的眼睛濕了,我用低到自己才聽到的聲音說:「記住了,我決不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