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陳炯明故居
像是快要天亮的樣子,進來了兩個人。各背一管長槍,粗暴地將我提起來,不發一言,將我推向門外,推下樓梯。不到幾分鐘,便來到了軍閥陳炯明的故居,現在的公安局。
經過幾度改裝的高大鐵門中開著一扇僅可容一人進出的小門。剛跨進門,在朦朧的樹影中颯地站出兩名荷槍實彈的紅衛兵。
「站住!坐在地上!」
他們中一個鄭重其事的用槍進來。
車房本來沒有窗戶,門一打開,從完全的黑暗見到十足的陽光,眼睛幾乎不敢完全睜開,雖然沒有帶備牙刷和毛巾,但總不能放棄幾天來第一次見陽光的機會。
車房在兩列平房的轉角處,當我跨出門口時,我覺察到每個視窗都擠滿了人,他們顯然發現了一張陌生的面孔。我低頭走向井邊。井水清澈而且似乎散發著一種沁人肺腑的新鮮氣息。我迫不及待地將小水桶拋向井中,幻想著將滿滿的一桶水從頭淋下……小時候,屋子的後門便有這麼一口神奇的水井,一年四季供四十幾戶人家食用,永不枯竭。夏天,在海中暢遊回來,穿著「三角褲」,走到井邊,從井中提起滿滿的一桶水,奮力托上頭頂,一傾,嘩的一聲,涼浸浸的水飛濺而下,流經唇邊的水,讓人嘗到了淡淡的甘甜,海水的鹹味盡失,暑氣全消……
但是,我已提不起小木桶,因為稍一用力,浮腫的手背便有崩裂般的痛楚。我抖動一下繩子,將水桶的水減半,還是提不起來。最後,不得不失望地將空桶提回。說是空桶,其實尚殘留一小碗水。我欣喜若狂,飛快地捧起小桶,一飲而盡……
在有些角落裏常常到這裏來開會,卻從來也不曾注意它的細節。現在,這軍閥陳炯明的故居在我的眼前卻變得陌生起來了。
在高高的圍牆內,北、東、西三面是廂房——也就是現在這十多間擠滿了人的牢房。中間是建築的主體,它是一幢建築在高高的台基上的平頭整臉的四方形二層樓。窗戶寬大而且眾多,不過,都關閉著。它的主人早已不在人間,但它卻平穩而莊重地經歷了軍閥混戰時代,國民黨時代以及我們這個解放了的時代。任憑世界怎麼變動,怎樣喧囂,他都堅定地沈默著。
幾天來,我第一次有了打開手銬大小便的機會,我自然故意把腳步放慢,並且故意象初到一個陌生地方那樣東張西望。
主樓向南,前庭頗為寬闊。院中雜植花本,曲徑通幽。池水乾涸了,假山長滿了青苔,樹木不時飄落下來,平靜、肅穆、幾乎沒有一點聲息。
但是,生命與活力在光明正大的場合被禁錮時,卻是另一種方式在暗淡汙穢的角落裏表露出來。
在廁所的壁報上,正展開熱烈的爭論。
「大家來討論,」發起人用通欄標題寫道:「大便所裏可以不可以小便?」
這個問題十分奇怪地引起了十分熱烈的響應。
「大便有大便所,小便有小便處,到大便所裏小便,這不混淆了大小便的界限嗎?」一個善於「區別對待」(一條十分重要的政策)的讀者出主意了。
「我是學生,被當作階級敵人抓進來了,難道在廁所反而有區別對待這一條?」
「要是集中開會,小便處人太多,不是暫時也可以到大便處去一下嗎?要不然,遲到了,犯了紀律,不是又挨批鬥嗎?」一個遵守紀律的模範讀者擔心起來。
「喂!別操心呀,小弟弟!你屙得滿地是尿,人家怎麼大便呢?不如暫時到女廁出,哈哈!那裏人少!」一個善於區別大小便界限而不喜歡區別男女界限的讀者指教著。
「你才去呢!」從字跡上看,分明是『小弟弟』在害羞地反駁著。不過,自上次他發表了意見之後,很多意見又加在下面,所以,他不得不在他回答的前面引了一條長線到不分男女界限的讀者那裏,並用箭頭指住它,算作對它的答覆。
「怎麼不可以呢?你怕什麼!只要思想正確,立場堅定,那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這似乎是蹩腳的政工幹部的語氣。
「其實呢,大便處不准小便只是一句空話!我就親眼見過許多大人物在大便處小便,更有在小便處大便的。但我是『下司』,不敢開口,還是少說為佳!」一個恭順的「下司」寫道。
「太無造反精神!」他馬上遭到造反派的苛責……
這些,都是誰寫的呢?他們每天關心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呢?
時代是偉大的時代,地方是嚴酷的地方,一個令人掩鼻而過的題目卻那樣地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並且是那樣的神氣活現,興趣盎然。
我感到惶惑,感到茫然。
首長們我剛回到車房,後面又吆喝著「出來!」
一個帶紅衛兵袖章的青年又把我帶到這列平房中唯一建在高臺上的房子。打開了門,便把我推進去。我跌落在坐著的兩個人中間,一胖一瘦,仔細一看,胖的是造反派所擁護的副縣長,瘦的便是我們竭力保擁的當今縣太爺!
瘦長的縣長顯得更加清瘦了,文弱女性化的溫柔,光著這外表,很難相信這是經歷過四十多場鬥爭而毫不妥協地站穩了「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人。
他是以「叛徒」的罪名被抓進來了,那是因為在檔案中查到他曾以地下黨員的身份到過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既然如此,天下的造反派幾乎可以完全一致地提出以下的問題:如何屈服於白色恐怖?出賣了哪些革命同志?如果你無法提出你二十多年前沒有做錯事的證據,你便必須認罪。而如果你認了罪,你便必須在專案人員的「啟發」下創造一些證據,以便人們如獲至寶般帶著這些證據走遍天涯海角落實——因為我們是重證據,重調查研究的。這樣經過內查外調的結果,終於順籐摸瓜揭發出了更多暗藏的階級敵人!於是,理論家們便根據這些觸目驚心的事實,得出階級鬥爭日益尖銳複雜,甚至,連夫婦、父子之間也存在著階級鬥爭的結論!
遙想當年風華正茂,懷抱著解放全人類的理想,脫離了剝削階級的家庭,經過幾十年出生入死,艱苦奮鬥,終於做了人民父母官,現在卻落得這樣的下場!
「公安局的大鐵門是他們怕檔案被搶,做報告由我批款加固的,現在卻用來關我;看守所的圍牆,也是我批款加高加固的,最後,恐怕連我也會被關在裏面」
這樣的推論,使我感到悲涼。一個堅強的馬列主義者,有時甚至陷入唯心主義的宿命論中。
他已經五十多歲了,唯一的希望是有朝一日得到革命群眾的諒解,回鄉放牛牧羊,這也是古往今來書生們最好——也是最壞的退路。
他雖然覺得自己的命運已無足輕重,對於我卻關懷備至,時加勸勉。
「你年青有為,出身好,又是經過四清運動的考驗入黨的,黨瞭解你,革命群眾瞭解你」他沉吟了一下「而且你的問題發生在國內,省內,不出十天半月,便會有結論的!」
稍有歇息的時間,他便用他隨身攜帶的國公藥酒為我拭擦和按遍體的腫瘀與傷痛。我的內心長久地洋溢著在慈父的守護下安渡風暴的感覺。
胖子是剛提拔不久的副縣長,他原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科長,由於中四清運動中大力揭發了他的表親——四清運動下臺的縣長的地方主義罪行,因而越級提拔,可是因為過份推崇,大革命時期當地的革命運動,頗有毛主席所領導的秋收起義之嫌,被我們這一幫革命左派揪了出來。
這樣,兩派都各自抓住了對方的後臺,並且迅速地與自己被的後臺「劃清了界限」並且同時宣稱:「受蒙蔽無罪,反一擊有功!」
胖子的特點是:睡得足,吃得飽,屙得多——這好像是造就一般胖子的各種因素。只要是腦袋觸及枕頭、被或者任何可以倚靠的地方,他就立即呼嚕呼嚕地打起鼾來。對於那些橫恆在一般人心頭的問題,他好像處之泰然。他完全沒有感到悲哀、愁苦或沉悶的時候。
處在這兩人之間,夜裏總是睡不著覺。向著這邊,縣長徹夜抽煙;轉過那邊,副縣長鼾聲雷動。
胖子的左邊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兼郵電局長。也是我們的「戰友」。
他有一個方臉,一張刻薄的嘴唇,鼓脹的雙頰。
他的罪名真多,造反派的大字報曾這樣開列:
革命的叛徒——在遭受革命群眾鬥爭時竟敢跳樓自殺(未遂);
四清下臺幹部——四清犯錯誤、降二級;
國民黨特務——在某處發現與他同名同姓的國民黨證,據說家中保存了青天白日旗(這一點要徹底交代!)
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保皇派的黑後臺,與造反派對著幹。
歷次政治運動並沒有使他的靈魂有多少觸及,甚至也改變不了他高傲刻薄的個性。他著重總結的是:被打的教訓和免於被打的經驗。可惜當他誠意地傳授給我的時候,卻是我被痛打過之後。
每個房間都上了鎖。只有早上洗臉的時才輪流打開。當然,每天都有各房間的人被揪回原單位批鬥或到來索取坦白交代材料。
光陰如輪轉。它在各種不同的角落裏都以同樣的速度輾轉過去。它對於好壞良賤的各種人們,都賜予同樣式的黑夜和白晝,同樣的陰晴冷暖。但是,在這裏,人們卻都無端地覺得日子過分的漫長,空氣格外的沉悶。
人們的心靈經常地深藏著隱憂,眼裏經常飽含著淚水;即使有片刻的歡笑吧,那也是一種變態的、哀戚的笑。
在這裏,歡笑只是眼淚的延續,怨恨、煩惱、狐疑、失望、恐懼統治著每個房間。
實際上,各人在這裏只是一個過渡。十天半月之後,每個從這裏出去的人都將懷念這個不可多得的天堂!
雖說不準亂說亂動——這一條就足以將我們這一群定性為敵人——不過與後來的任何地方比較,這裏的生活已是相當的機關化。這也許因為囚禁的多為各種幹部而管理者又多為如我們一般的保皇派之故。
每天早上五點半哨子聲催你起床,坐著輪候洗臉。八點鐘吃早飯,然後輪候大便(每次三男二女),小便則可隨時舉手報告。可以看毛選、寫交代材料、或者什麼也不幹,但絕不能躺下睡覺——這一點對於胖子副縣長實在是十分殘酷的規定,倘在外面,這細室是他堅決造反的條條框框。在這裏,則只好恭順地聽著紅衛兵們的吆喝和責罵!政治部主任則忙於用煙紙慢慢地捲土煙絲。然後,慢慢地一口一口的享受著,循環往復。我與縣長則閱讀著他帶來的毛選(顯然,被抓進來之前,他有充足的準備時間)。
我一直希望對毛選有一個深入的瞭解,我也背熟了所有的毛澤東詩詞。如果用些力氣,相信會有一些心得。可惜我再也沒有這樣的時間了。
有一天,房門被打開。叫的是我的名字,幾個人都有些吃驚。政治部主任馬上暗示我:要避免對抗和挨打。我膽怯地望瞭望縣長。縣長慈祥地望著我:「不要怕,相信黨的政策!」這雖然是一句普通的「官話」,但出於他之口,也就使我安定了許多。
兩個人在亭子裏等我,一派斯文淡定,雖然也用著攻心戰,但並非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顯然與那些以自己是個大老粗為榮者完全不同。我相信他們的級別較高,可以說理。
他們直言不諱地聲明他們屬於地區公安局。我發現他們已作了全國性的重點調查。這令我十分放心。因為以他們的能力,完全可以為這案件作出否定的結論。
令人驚奇的是:他們居然談到了我在《長江文藝》的投稿和我與《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幾次通訊。那些通訊主要是談論對我的兩篇小說稿的修改——修改的要點是我認為是故事賴以開展的基本風格而他們稱之為「陰沈灰暗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地方。
那些信件本來收藏在家裏不顯眼的地方。我想,我已被抄了家!如果他們不能將我定為「反革命」,那麼,憑著我支持K君的偷渡和我「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也就可以向「革命群眾」說明我罪有應得,他們並未抓錯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或者可以不被判徒刑,但可能是: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開除出隊。那麼,我將要求讓我回故鄉,鈞魚為生!
似乎已經有了一個結局。所以,當我向他們告別時,心情也輕鬆了許多。
我將要渡過人生的三十人寒暑了。我從未追求過金錢與地位,我的唯一願望是:我能夠從事文藝工作,我幻想著那樣可以對國家社會有更多的貢獻,那也是我的興趣所在。除此之外,從事何種工作對我都無所謂。
貌似平靜的生活,不久便被打破。
一天早晨,天還沒亮,朦朧中聽見縣長在輕輕地呼喚我,當我睜開眼睛時,他指了指對面:「彭X自殺了!」
我吃驚地坐了起來,縣長深沉、猛烈地抽著煙,政治部主任往往復複地搓弄著煙捲,胖子低著頭,破例地沒有靠牆斜坐。
彭X即四清下臺的縣長,中共成立初期的領導人之一的兒子。下臺後調省城做一個大學的某系的支部書記。想把他抓回家鄉批鬥,苦無藉口,終於,有造反派查到他的父親是叛徒,出賣過革命,所以將他揪回來,就囚禁在我們對面的一間房子裏。單人,被嚴密監視,不能出房門。
大約半個多月吧(那時我還未被抓起來),決定開一個空前的批鬥大會,批判彭X。各派參加,並且揭發、批判、鬥爭。
因為他父親是叛徒,自己又為三反分子(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各派都爭取表現,力圖證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
這一天,自然,全城都停止了工作和生產,城郊的農民也放下了犁鈀,各主要要街道橫掛著紅底白字的布幅。上面寫的是目下最流行,最上綱上線的標語:
「鬥倒、鬥垮、鬥臭彭X!」這樣的標語通常將被鬥者的名字倒掛並加XX。
「打倒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彭X!」
「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
「打倒修正主義的總後台劉少奇!」
「打倒帝、修、反,打倒國內外一切階級階級敵人!」
「誰敢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砸爛誰的狗頭!」
這樣的事情通常由「大批鬥領導小組」負責。而我們和一些單位的領導人只是提早到會場檢查準備的情況。當口號聲漸近的時候,我便開始注意廣場的入口處。
走在最前面的是手執紅色語錄的工農兵代表。他們正高唱著簡單而容易上口的語錄歌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
「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呀呀嘿!」
兩排掛著「紅衛兵」袖章,手執各式自製刀棍的糾察隊從他們兩旁伸展下去。
彭X終於走到我們跟前。我到X縣工作時,他剛好離開,所以一直沒有見過,根據大量的揭發材料,我想像到他應該是堅強的、頑固的、桀傲不馴的。沒想到竟是一個廋骨嶙峋的文弱書生。臉色蒼白、眼神迷惘。南方八月的驕陽曬得他汗流浹背。他的頭上戴著尖尖的高帽。背後插滿白色三角旗。每面旗開列一項罪名,在震天響的口號聲中,他不時閉起眼睛,任憑人們推拉打罵
在彭X的後面,跟著一群今天陪鬥的牛鬼蛇神,他們更具特色。劇團的當權派被化裝成秦檜以示「內奸」,飯店的走資派掛著豬腿以示生活腐化墮落,汽車站的死不悔改走資派戴上車頭燈殼以示有眼無珠,建築材料廠的右派頭上疊五塊黑磚以示「黑五類抗拒改造」……
在喧鬧中,忽然聽見陳師傅在高喊著「X司令!」只見他眉飛色舞,胸前掛著五、六個毛主席像章,其中一個足有拳頭那麼大,像是一面護心鏡。他怎能不興高采烈——今天鬥爭性的人與他非親非故,而且是一個反革命,一個想要使千百萬無產階級人頭落地的階級敵人!他握緊拳頭,振臂高呼,驕傲地從我面前經過,這使我十分放心——今天,似乎不必擔心他在會議中間打開毛主席語錄,要大家跟讀:「說話寫文章要簡明扼要,會議也不要開得太長!」
緊隨而過的是工人,居民和進城的農民,人數號稱十萬!
彭X和他的反革命集團、黑幫站在臺上,他們的背後都有兩個紅衛兵監視著。他們都必須雙腳併攏,彎腰低頭,這叫向人民低頭認罪,或向毛主席請罪。這是在任何批鬥會上換批者都必須做到的標準模式。
人們按照預先編排好的次序和所分配的題目,自覺地懷著對階級敵人的強烈仇恨,檢舉,揭發和批判。
他有什麼罪呢?他的罪似乎來自他的父親和祖母。
他的父親是中共的第一批黨員,在當地領導過農民起義並建立了蘇維埃,這本是當地人民及他的後代引以為榮的。但是,幾個月前突然發現被國民黨逮捕並英勇就義的父親是叛徒,並且出賣了革命同志。
父親是叛徒,兒子也好不了多少,起碼,骨子裏也難免有反動本質,這是第一條罪。
他的祖母在解放後作為全國軍烈屬的代表上京開會,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接見後毛主席和周恩來、劉少奇等人與全體代表一起照像。祖母被安排在毛主席身旁坐下。回家鄉時,老人家頗覺榮耀。讓人把他與毛、周在一起的部分放大,十多年來一直掛在客廳。這一次紅衛兵抄了家,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一分析,非同小可!照片戳了毛、周在兩旁她在中間的一段加以放大。把自己當成國母,篡黨奪權之心昭然若揭。
再翻翻歷史老帳,彭X祖輩,原是當地有名的大地主,這一下,批判者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加以分析,彭X這個地主階級的老子賢孫處心積慮,妄圖實現資本主義復辟乃是理所當然的事!這是第二條罪狀。
當然,也有一條大罪似乎牽涉到他本身。即,他一直以來多次宣揚當地農民運動的意義,蒙蔽了廣大群眾。而這一點的本質是什麼呢?是把他父親所領導的農民運動淩駕於毛主席的秋收起義之上,貶低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的豐功偉績
分析批判至此,群情洶湧,個個觸發了對毛主席的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
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砸爛誰的狗頭!
彭X反對毛主席罪該萬死!
臺上的紅衛兵對彭X高喊著:「向毛主席請罪!」然後強力地把他的頭按低,當頭顱觸及地面的時候,彭X終於支援不住,噗通一聲,撲倒在地上。人們迅速揪住他的衣領,把他提起來。只見他鼻血不斷地流淌著,臉色由青轉白。
「快把你反對毛主席的罪惡勾當交代出來!」
「抗拒交代,死路一條!」
「認罪!認罪!」
他仰起了頭,力竭聲嘶地喊道:「我——無——罪」
立刻,所有的紅衛兵都湧到他的面前,把他高昂的頭一直按到地面。很長時間,他再也起不來了。但批鬥照常進行,口號照常呼喊,拳頭照常揮舞。我覺得暈眩,幾乎無法無法感知周圍發生的事。
終於到了散會的時候。將彭X揪起來時,他已無法站立。
彭X頑抗到底,死路一條!口號聲繼續轟響,與臺上的火候配合得天衣無縫!
彭X被兩人連扶帶拖地弄到台下,然後,大隊人馬出發繼續遊鬥。
從此,不再全縣批鬥了。改為今天這個派鬥,明天那個團批,大約也忍受半個多月吧,昨晚終於趁著看守不備自縊身亡。
自然,這類事情被認為是堅持反動立場,自絕於人民!
自此之後,對我們的管理也嚴格起來了,深恐有誰再堅持反動產場,自絕於人民。
這一天,是10月24日,兩點鐘,突然響起了一陣長長的哨子聲。
收拾好自己的東西,到外面集合。
我們都驚喜交集,不知何去何從,反而是政治部主任冷靜地分析:
「從法律的觀點看:逮捕要有逮捕證;扣押需向本人及家屬宣佈;拘留不能超過24小時。這樣長期不明不白地關起來,自然不行,需釋放至原單位——最多是在單位隔離審查!」
我對此頗有懷疑,因為這一切早已被造反派當作資產階級的條條框框加以破除。因為按照憲法,我們幾個人誰也不必到這裏來。不過,縣長勸我還是往樂觀處想。所以,我們一邊收拾東西,一邊道別,相約後會有期!
但是,到了外面,氣氛完全不同。我們被命令坐在地上,聽一通語錄,諸如:
「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然後,武裝部長表示為了形勢的需要,我們必須分兩批轉移到不同的地方去。
縣長、副縣長、政治部主任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被叫了出去,並且被四個帶槍的紅衛兵帶走。可以猜測的,似乎這些人多是歷史複雜而未能作結論的人,當我的眼光與縣長的眼光接觸時,眼淚也止不住流了出來。我覺得他真的老了,我多麼願意與他囚禁在一起啊!
不過,我們留下來的人,遭遇並沒有更好。我們同樣被帶槍的紅衛兵押走。當我艱難地背起沉重的行裝時。我才又重新感覺到我的胸骨和兩脅的致命的傷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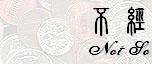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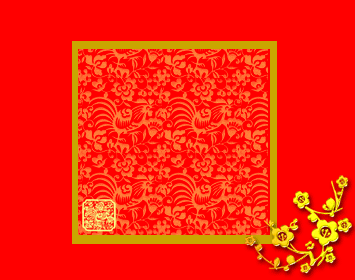
好吧,我只好每次都從頭看起了。
大哥,可否更新得快一點呢?一個星期才up date 一次,害得我又要將之前的重新看過一次,再接著看更新的。